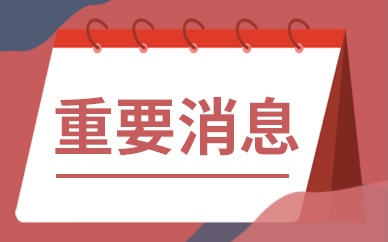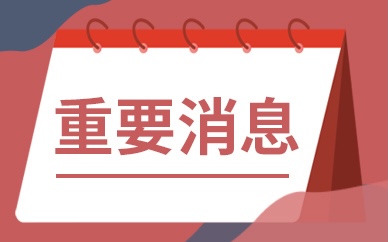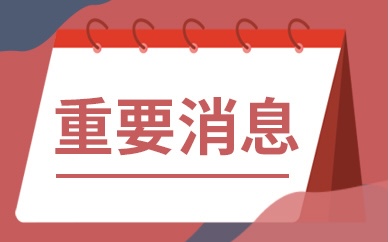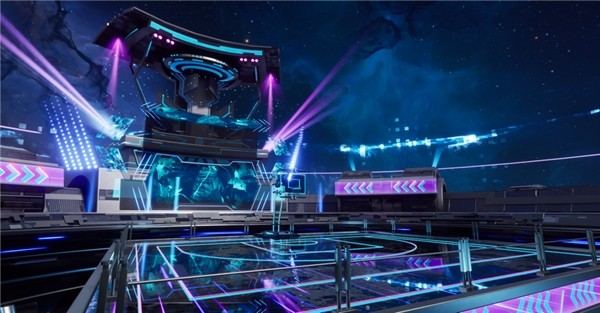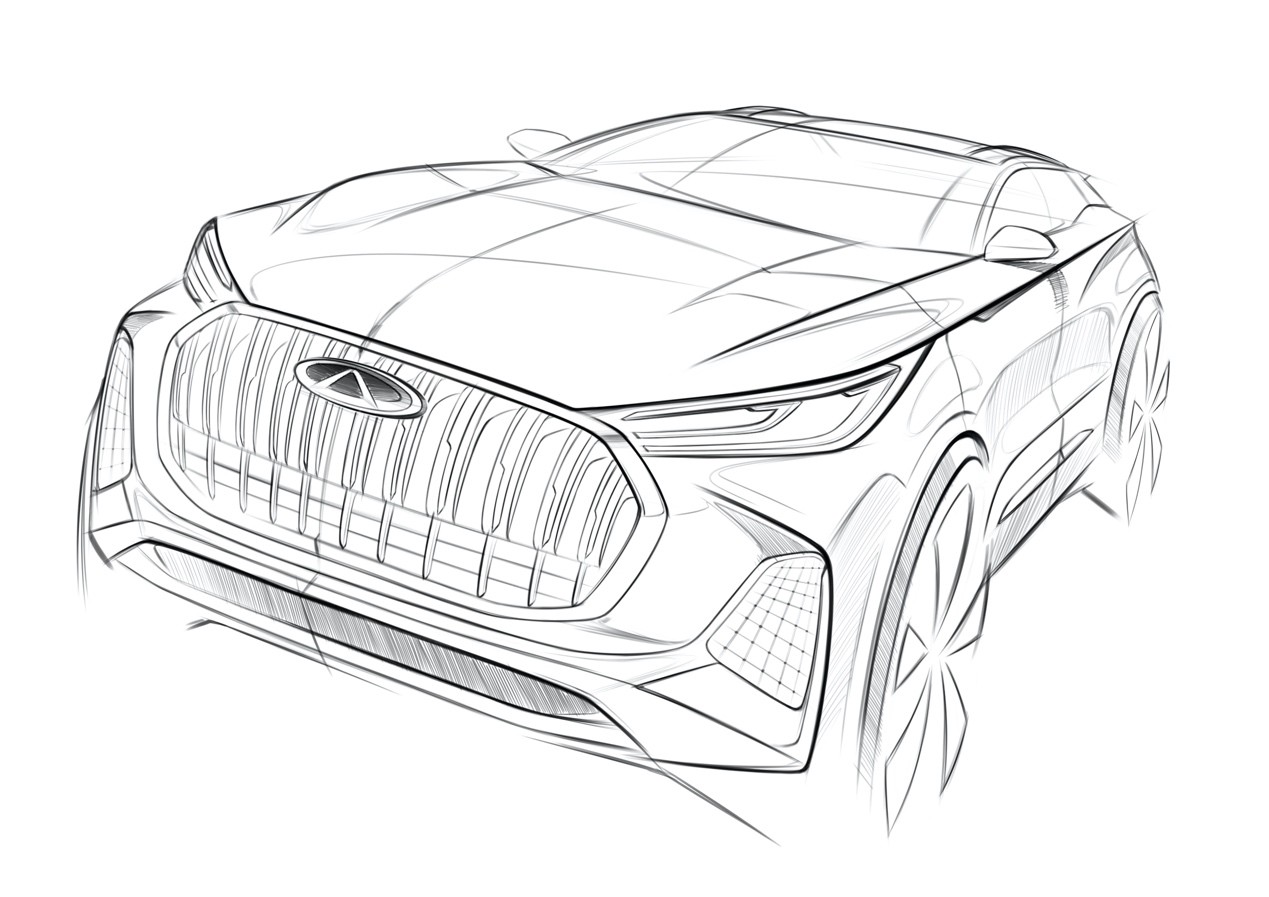作者:王晓莉
有一回打车去看外地来的朋友,路途远,又下着雨,车开得相当缓慢。在那样的情形下,和出租车司机聊聊天不失为一件可以解闷的事。
司机四十来岁,和大部分出租车司机一样健谈。他告诉我他是离异男,带着个九岁的女儿。“其实经济上过得去,女儿还可以在街道办事处吃补贴。就是心累。”
 【资料图】
【资料图】
“我女儿近视。”他说,“一千度,矫正后的视力小于0.3,可以领残疾人补贴。”
我才知道,原来高度近视也属于残疾。
司机拿出钱夹子,透明薄膜里夹着他女儿的照片:一个扎马尾辫的小女孩,戴着副镜片极厚的眼镜,就像我们俗语说的,跟酒瓶子底似的。因为镜片厚的关系,她看起来少了点儿童的稚气,多了分深深的专注。
我想起了老钟伯伯。
从前,我住在一个大杂院里,老钟伯伯是我的邻居,很疼爱我。他高度近视,看什么东西都要皱起眉头,微眯着眼睛。即便眯起眼,还是只能看个朦朦胧胧。走在路上,即使我与他迎面相遇,他也是认不出我的。每回都必须是我主动喊他,他方才如梦初醒地看着我,然后叹一口气:“唉,近视眼,可怜哪!什么都看不清!”
也许越看不清楚,就越喜欢看。老钟喜爱看人。“啊,你今天穿了条好漂亮的花裙子。”他常常这样善意地夸赞一个迎面遇到的女邻居。但是一般也就到此为止了,因为再夸下去,他便完全说不清楚女士的花裙子上究竟是印了小鸟还是海棠花。
每逢这种时候,不了解的人不免要多嘴一句:“干吗不戴眼镜呢?”
我们这个大杂院里的人都知道,老钟的习惯是,如果不看电影、不看书报、不吃酒席,他就坚决不戴眼镜。“我一个搬运煤球的,不想人家叫我‘四只眼’。”老钟说。在那个年代,人们称呼戴眼镜的人总是用这个有点被瞧不起的外号——“四只眼”。老钟在街道的煤球厂做事,像他这样的体力劳动者,常年在外干活,逢到刮风、下雨,灰尘大或是雨雾浓重,戴着眼镜也很不方便。
老钟的眼镜装在一个硬盒里,他总是揣在他的上衣兜里,衣兜上的小扣总是扣起来。遇到必须要看清楚东西的时候,他才郑重其事地解开那粒小扣,取出眼镜盒。每回他戴上眼镜之前,即使镜片已非常透亮,他还是要对着眼镜哈几口气,用软布仔细地擦一遍,仿佛多擦一道就可以把这个世界看得更清晰一点。待到看完了要看的东西,他又郑重其事地把眼镜放回盒子里,揣在衣兜里。
老钟必定会戴上眼镜的时候,是去吃酒席时。被人宴请的机会太少了,因此老钟非常珍惜。
他在上第一道菜之前就已经取出了眼镜。等主人或是餐馆营业员端上菜来,他几乎同步地戴上。他比谁都仔细地看着、研究着盘里的菜色。他的眼珠子仿佛可以前后伸缩似的,突出来又收回去。等酒席散去,我们所有人都忘记吃了些什么,只有老钟,可以准确地报出从第一道菜到最后一道菜的所有菜名。
谁也不知道老钟的眼镜度数究竟有多深,因为谁也取不到他揣在衣兜里的眼镜。只有一次,他喝多了,竟然允许我把玩他的眼镜。我生怕他反悔,把那“酒瓶子底”急急地放到自己的鼻梁上,一瞬间,我的眼前一片眩晕。
老钟视力欠佳,但心善在我们街上是出了名的。有一次他骑自行车路过一所小学,正逢课间休息,许多学生蹲在校门口的地摊前买小零食或翻小人书。上课铃响起,大家起身就往校园里跑。老钟近视,反应略慢,来不及刹车,一个奔跑的孩子与他的自行车剐蹭了一下。孩子继续往前去了,老钟却没有走,他赶紧下了车,找到校务处,费老大劲总算找到孩子所在的教室。他戴上眼镜远远看一眼,见那孩子端坐无事,这才离开,去办他那已耽搁多时的事。到了晚上,老钟又找到了孩子的家。邻居们知道后都说他:“学生没事,你还去人家家里,想惹点事还是怎么的?”老钟说:“我就是有点不放心。一是去看看后续,二是跟人家家长解释一下。”邻居们都不作声了,老钟就是这样的人。
老钟因为高度近视,直到四十岁才结婚。他的妻子是个常年坐在轮椅上的女人,脸上长满了雀斑。大杂院里的人说话总是很直接,有时就拿老钟和他老婆的雀斑开玩笑。多嘴多舌的拐子李有一回说:“老钟你发现没有,你老婆的雀斑不是和别人一样随意地散布在脸上。她是以鼻梁为中心,向四面放射的。”老钟一点也不生气,说:“我反正不喜欢戴眼镜,所以每次看我老婆,都觉得她还蛮漂亮的。”
每天早晨,老钟蹬着一辆自制的带拖斗的小车,把妻子送到百货大楼后面的小街上。那条街聚集了不少我们这个城市的手工缝纫女,人们有什么要缝缝补补的,都会送到那条街上去。老钟的女人就在那里接活儿干。
我忘不了每天早上上学时,与蹬着拖斗车的老钟相遇时他的模样。因为高度近视,他不能灵巧地回头或旁观他人,他总是非常吃力而专注地看着前方,好像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似的。这时他总是戴着眼镜——他也顾不得成“四只眼”了。那眼镜厚得摔也摔不烂,架在老钟硬挺的鼻梁上,整个人如同一尊雕塑,让我想到戴眼镜的狮身人面像。
在早上一大群匆匆忙忙的行人中,老钟总是一眼就被我辨认出来。还是小女孩的我,见到父母的婚姻,见到其他邻居的婚姻,又在老钟专注而吃力地拖着残疾妻子去上工的画面中,模糊地感受到婚姻还有另一种温馨的模样。
到了老年,老钟的近视越来越厉害,有时他甚至不得不拄拐而行。即使戴上眼镜,他看一份报纸的样子还是显得非常可笑:报纸和他眼镜的距离最多只有八厘米。他像一只特大号甲虫一样地扑在那份报纸上。
和所有到暮年都会开始思索人生要义的人一样,老钟渐渐关心起灵魂与信仰这些“务虚”之事。由于高度近视,他并不像他人那般轻松与放松。他总是被一个问题折磨:如果人有灵魂的话,我的眼睛这么差,将来我的灵魂的眼睛是不是也看不清呢?
邻居们想方设法安抚他,但都不管用。
有一天,我爸爸特意跑去问他:“你在梦里看不看得清楚呢?”
老钟说:“嗨,奇怪了,我在梦里连几米外飞着的小蠓虫都看得清清楚楚。”
我爸爸说:“那你放心。梦境和灵魂是最接近的。你的灵魂的眼睛一定比你现在的眼睛要好上不知多少倍。”
为了这番话,老钟特意拄着拐棍去市里最有名的“钟鼓楼”食品店,买了两斤绿豆糕来谢我爸爸。
老钟一直给各家各户送煤球。到后来,人们渐渐用上了蜂窝煤。再后来,煤气开始覆盖这个城市。只有特别节俭的小店铺才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煤球。老钟的生意越来越冷清,但只要有人家订煤球,老钟就会热情地一一送上门。
那些订煤球的人每回见到高度近视的老钟,都会不约而同地说:“小心啊,老钟。”
老钟一边搬着一摞摞煤球一边说:“没事,老王(即我爸爸)都说了,我灵魂的眼睛好着呢。”
常常话没说完,他就摔了个趔趄。
但是没有一个人笑话他。谁都知道,老钟的心眼好——心眼,就是灵魂的眼。
老钟说的并没错。
几十年过去了,现在我自己也戴上了眼镜,且随着读书、用电脑、用手机,眼睛的度数在一天天加深。有时我揉着酸痛的眼,或者突然意识到又必须换一副度数更深的眼镜时,早已去世的老钟就会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老钟这样一个双眼视力不健全的人,心眼却柔软得令我记了他一辈子。
不禁又想,要是老钟在世,他也应该和那位出租车司机的小女儿一样,吃上街道办事处的补贴了吧?
《光明日报》( 2023年03月17日 15版)
关键词: